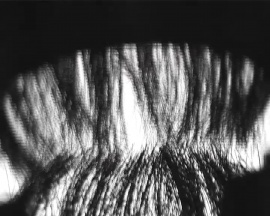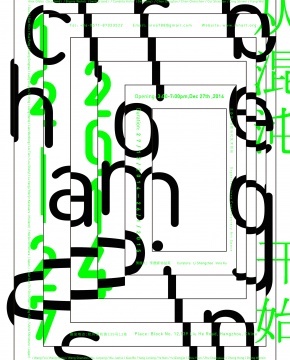“就让我们从一团混沌开始吧。”——杜尚
1957年,在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,情境主义国际(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)正式宣告成立。随后的十五年间,情境主义国际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描绘并抗衡着“景观社会”(Society of the Spectacle),不断探寻着艺术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、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方法,实验各种将景观社会颠倒为艺术“瞬间”的革命实践。将近六十年后的今天,当初德波(Guy Ernest Debord)所描述的现实: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生存方式上已经从存在堕落为占有,而景观社会又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了表征”,却还依然牢牢的把我们囿于其中,甚至比起当年更加的无孔不入、进化的更加潜形匿迹。对于当下的“现实”,我们不断辨认又不断模糊,不断抗拒也阻挡不了不断地被异化。然而,无论如何,期许历史有机会重新开始,是一种不可能的妄想;简单的重复历史上的方案也不适时宜。对于我们来说,面对的只有这个叠印了无数抗争痕迹的当下,只有这个无法和海水脱离的海平面。没有一个纯粹的、可以切割的原初可以回返,也无法去希望于一个忽然坠入的完美的他者来使我们获得救赎。也许,只有当我们割裂所有用来幻想、逃避、移情的可能性;当我们承认无路可退、无处可去时,那个真实的此在,那个你双脚所覆盖的地面才开始真正的清晰和坚硬起来。这个万重纠结的、复杂不堪的此地,便是我们行动的立足点。
那么在今天,艺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立足点,可以或者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艺术区别与其他学科有什么独特的力量?我们总是不厌其烦,一次次自问着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。
萨拉·马哈拉吉(Sarat Maharaj)教授曾在文章中比较区分了两种知识:有章法的知识与无章法的知识。从而引出了“作为知识生产的视觉艺术”这一概念,他认为这种知识生产的认知引擎就是“通过视觉去思想”,“通过视觉去思想”区分于另一种“将视觉系统建立在语言模式上”的减缩的“视觉思考”方式,虽然也会和现有的语言模式发生借用和互动,但是更多的是想要逃离出语言的边界之外,从而进入那个未成形的、混沌的阴影地带。“通过视觉去思想”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类型的思考方式,它不属于任何的学科地带,萌生于“任意”空间——无处不在,并与“有章法的知识”系统完全不同,是潜在可能性和倾向性难以预测的涨落。
由此,当我们面对着景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、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这样的一个现状和困境中时,通过视觉艺术所拥有的这种可以进入创造性的混沌状态、非“体制化的冲动”的特性,我们隐约可以寻觅到一条散落着微光的艺术特有的可能性之路。在景观社会中,感知尤其是视觉是其中重要的媒介和方式。所以在这个现实与景观相互异化的通道里面,艺术能否像一股无法捕捉的、无法定义、变幻无常的气流散布、弥漫在通道里面,它打散、拆分原有的图像、符号、空间与时间之间的联系,挪动“常识”的边界,扰乱正常的秩序,不断催生新的感知结构?创造性的混沌状态,类似于巴丢(Alain Badiou)所说的“黑夜中的伏兵”:它是潜在的、无目的的、无法预测的,因而也可能携带出最大的潜能和意外。
我们且将这次的展览视为一种混在时代噪音背景中的讯号,它源源不断的发出并且召唤那些用艺术尝试并进行着各种“知识生产”的人——甚至这种认定都未必那么明确和重要。在展览中,我们希望建立和呈现的是一种不可归纳的、有异议的共识形态。重新回到混沌并不是说我们要像盘古那样“劈开混沌造区宇”,对于我们而言,没有一个点式的“区宇”的存在——无论它是劳作的终点或者是世界的起点,没有一劳永逸的一次性完成的时刻。我们需要的是“一再”,不断地出入于混沌间,不断的警惕各种习以为常的“常”,从每一个海平面的微小的褶皱中掀开,反复出发,永无止境,无限和无穷便凝聚在这种反复之中,就如同西西弗斯(Sisyphus)的汗水凝结的闪光,这绝非是一种无用的徒劳。他是幸福的,用一段有限的路程折叠出了无限:从混沌开始,没有终点,目的地(如果有)在很远的地方。
李晟曌
2014
收起